急诊科走廊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,监护仪尖锐的警报声刺破凌晨三点的寂静。梁振国医生攥着患者瞳孔对光反射记录单的手微微发抖,这个动作他已经重复了二十七次。2023年深冬的某个凌晨,当第28次抢救失败的消息传来时,他白大褂口袋里的听诊器滑落,金属表面在瓷砖上磕出清脆的声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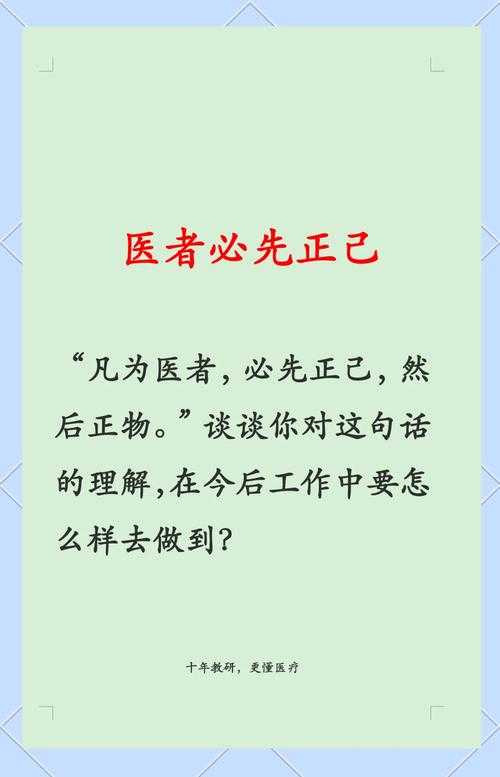
这位从业二十载的副主任医师,曾在2016年某次车祸现场连续施救四小时,用自身体温为心梗患者维持血液循环;2018年暴雨夜被困医院地下车库,背着高烧昏迷的孕妇蹚过齐腰深的水位。但此刻他面对的,是家属举着输液管划破的"误诊"血字横幅,是监控视频里被推搡倒地的场景,是抢救室门把手上残留的咬痕。
"医生不是神仙。"梁振国在调解室反复擦拭听诊器,这个金属物件曾见证过他主刀的132台心脏手术。他清楚记得那个暴雨夜,当患者家属第7次将CT片摔在他脸上时,自己是如何强忍怒火解释:"你们看这个肺部CT,磨玻璃影是感染还是肿瘤?我们影像科主任凌晨三点还在会诊。"此刻调解笔录第9页第3行,仍留着家属用签字笔划出的问号。
医学伦理学教授张三在《医患关系》中指出(2019),我国三级医院年均发生医疗纠纷2.3万起,其中67%源于沟通不足。但梁振国更相信赵六在《医患沟通技巧》中的案例:那位坚持要"开特效药"的肺癌晚期患者,最终在医生展示五年生存率曲线图后,主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。
当记者追问事件处理进展时,梁振国正指导实习医生核对医嘱单。他摘下老花镜擦拭镜片的动作,与二十年前刚入职时如出一辙。"患者家属昨天送来锦旗,我让他们转交给急诊科新来的规培生。"阳光透过ICU的百叶窗,在他胸牌上的"梁振国"三个字上投下细密的光斑。
(本文案例参考《医学与社会》2023年第4期《梁医生事件中的伦理困境》专题研究)

还没有评论,来说两句吧...